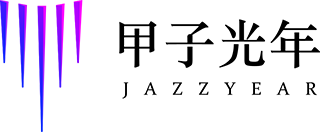当纤维本身具备感知与思考能力,技术便能以更自然的方式理解和改善人类睡眠。
作者|王博
深秋的剑桥,落叶在微冷的空气中打转。
走进MIT Media Lab(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,后文简称MIT媒体实验室)那座玻璃与钢的建筑,门廊隐约回响着实验室内的低频电子噪声,仿佛一台巨型合成器在呼吸。
 MIT媒体实验室,图片来源:「甲子光年」拍摄
MIT媒体实验室,图片来源:「甲子光年」拍摄
MIT媒体实验室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之一,以“反常规创新”著称。MIT Media Lab中的Media并不是指新闻媒体(News Media),而是科技媒介(Technology Media),实验室作为一个创新平台,鼓励科研人员跨越计算机科学、艺术设计、生物科技、神经科学、社会科学等边界,探索技术与人类体验的未来。Kindle的核心显示技术电子墨水E-Ink就是MIT媒体实验室最成功的从科研到商业化案例。
在这里有一句话:“Demo or Die(展示原型,否则无意义)。”这也是实验室内部的行动准则,与传统学界的 “Publish or Perish(发表或灭亡)” 形成鲜明对比。
我在这里要见的是约瑟夫·帕拉迪索(Joe Paradiso)教授:一个从高能粒子物理转战可穿戴感知,又从电子音乐跳入传感器世界的谜一般人物。
1977年,Joe Paradiso在塔夫茨大学获得电气工程与物理学学士学位,1981年又在MIT完成物理学博士学位,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基于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研究中心(CERN)进行的一个实验,内容与高能μ子对的产生测量相关。
可以说,1994年之前,Joe Paradiso都是一个物理学家。1994年,他加入MIT媒体实验室,并创立了响应式环境(Responsive Environments)研究组,三十多年来,他一直致力于让建筑、家具、衣服成为“有感知、自反馈”的系统。
除了科研与学术生涯之外,Joe Paradiso从1975年起就一直在设计电子音乐合成器,并创作电子音乐。他曾设计并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模块化合成器之一,被视为电子音乐控制器领域的权威。
而这次,我们要聊的是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。
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由Joe Paradiso教授团队与中国的慕思集团联合研发,其技术核心在于让柔性材料实现“感知—计算—反馈”的闭环功能。研究团队将尺寸小至0.9毫米的集成电路嵌入可编织的柔性电路中,使纤维能够实时捕捉呼吸、体温、皮肤电反应与微动信号,并通过优化的tinyML算法进行本地推理。
当纤维本身具备感知与思考能力,技术便能以更自然的方式理解和改善人类睡眠。
虽然这一技术还远未成熟,但已经证明了一种可能——智能可以以更低干扰、更自然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本文,「甲子光年」对话MIT终身教授、MIT媒体实验室学术负责人、传感器与环境智能研究室主任约瑟夫·帕拉迪索(Joe Paradiso)。
 约瑟夫·帕拉迪索(Joe Paradiso)教授
约瑟夫·帕拉迪索(Joe Paradiso)教授
1.一个“关于未来的预警系统”
甲子光年:Paradiso教授你好,很高兴有机会与你对话。能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和在做的工作吗?
Joe Paradiso:我是Joe Paradiso,MIT媒体实验室教授,同时也担任实验室的学术负责人。在这里我有几个角色,其中之一是负责响应式环境研究组。我们致力于设计有趣的新型传感器,并将它们应用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。
甲子光年:这些传感器具体会在哪些环境应用?
Joe Paradiso:应用环境非常极端,从太空传感器,到非洲、南美洲等地濒危动物身上的传感器都有。我们也关注建筑内的传感器以及它们如何从基本上降低能耗,更好地了解建筑内发生的情况之类的。我们还非常关注对传感器数据进行有趣呈现,而不仅仅是收集数据。同时,我们也关注人们如何接触这些数据,如何与数据建立联系。
甲子光年:在你眼中,MIT媒体实验室是一个怎样的机构?
Joe Paradiso:我更愿意把实验室看作是一个“关于未来的预警系统”。它具有高度的跨学科性,融合了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、背景和研究领域。
在这里,我们都在设想快速到来的未来,并试图构建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尝试利用即将出现的前沿技术来具体呈现未来的某些片段,而有些技术在几年后就会成为主流。
近期有一些校友回来,分享了他们过去的项目。是的,我们早早就预判到了像汽车导航这样的技术,还有很多东西。其实,很多传感器网络的技术都源自MIT媒体实验室的研究,很多早期物联网研究也是出自这里。
MIT媒体实验室一直走在前沿,但是现在要保持领先地位难度更大了。我们仍然在坚持,我们仍然在展望未来。
2.AI如何改变睡眠?
甲子光年:MIT媒体实验室的很多研究成果的确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我注意到你的团队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——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平台,听说这项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。我很好奇,技术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睡眠?
Joe Paradiso:我认为有许多技术可以用于睡眠研究,其中之一就是监测人们在睡眠时的状态。
监测睡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。就拿我们正在研究的智能纤维来说,这一技术源自LED行业,我们可以在一些物体上植入电路,使其变成纤维状,然后就可以将这种智能纤维编织到床上用品等物品中。这样一来,我们就可以监测人们睡眠时的移动情况以及各种动态变化,甚至监测身体在不同睡眠阶段可能发生的适应变化。
但也有一些技术可以为睡眠提供刺激。所以,这不仅仅是感知,还可以有驱动作用。比如在不同时间播放音乐,用轻微的电流刺激,我们可以构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提供反馈,帮助人们获得最佳的睡眠质量。
甚至,技术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时候该去睡觉。通过量化自我传感器(Quantified Self Sensors),在某个特定时刻,它会提示你可能是时候打个盹儿了,不过打盹儿时间必须有限制,因为你不需要睡太久,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醒来。MIT媒体实验室里有些人在研究这些动态系统,他们认为,如果你能“更聪明地睡觉”,感觉就会好很多。这不是说睡久一点或者睡一整晚就行,而是要“聪明地睡”。
甲子光年: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可以说是下一代的传感器技术吗?
Joe Paradiso: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融合了多个技术方向。
其中之一是可穿戴计算(Wearable Computing)。MIT媒体实验室有一个开创性的理念就是要把计算机融入衣物。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,我们的学生就开始穿戴显示器、计算机,或者具有无线连接功能的传感器,所有这些信息都会传输到当时还处于早期阶段的“云端”。我们很早就开始探索这一方向。
而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则是下一代将传感器集成到衣物中的技术。当然,这会涉及医疗应用,比如监测一些生理指标,也可以作为计算机接口,因为它能感知人们的动作。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睡眠监测,可以监测人们睡觉时的翻身动作。所以,我认为把电路做到纤维级别,尤其是用于传感领域,是非常有吸引力的。
甲子光年:如何把电路做到纤维级别?
Joe Paradiso:有几种方法。有些研究者尝试像拉聚合物纤维一样拉制纤维,在拉制过程中嵌入芯片。这种方法的良品率很难提高,不过这确实是很棒的研究方向,我很看好。
另一种方法是Cedric Honnet(响应式环境研究小组的研究员)正在研究的。LED行业已经在生产微小的灯带,他找到了一种方法让这些灯带变得更小,小到真正接近纤维的形态。所以,将传感器和电路嵌入到类似纤维的物体中,可以编织到衣物等物品里,这将把可穿戴计算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
我预计这一技术将会催生很多应用,这也是我们与慕思团队合作并思考该技术应用的原因之一。我认为它是一个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,将会带来很多新的可能性。
甲子光年:说到和慕思团队合作,你们会做什么?
Joe Paradiso:Cedric正在研发这些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。他了解LED行业,知道他们是如何生产灯带的。他还参观过深圳等地的工厂,这些工厂具备相关生产能力。他改造了自己的设备,能够进行这种精细化的工作,并与制造商合作进行生产。
与慕思合作,我们会尝试将这些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应用到与睡眠相关的物品中,可能是睡眠眼罩,也可能是床垫,这样我们就能获取人们睡眠时的移动情况和身体状态的数据,在上面可以设置多种不同的传感器,这是我很希望看到的应用方向。
甲子光年:双方团队未来合作的研究会集中哪些方向?
Joe Paradiso:MIT媒体实验室涉及很多不同的领域,而慕思则专注于睡眠领域,所以实验室可以从不同层面上与慕思一起研究睡眠相关问题。比如,睡眠监测、睡眠干预、睡眠材料等。实验室的发展速度很快,所以具体的合作方向取决于我们未来的研究重点。
 MIT与慕思集团智能纤维研发项目签约
MIT与慕思集团智能纤维研发项目签约
3.智能最终都会往边缘侧迁移
甲子光年:你一直倡导“让环境有感知力(Responsive Environments)”。这次FiberCircuits智能纤维是否意味着“感知”正从空间走向材料本身?
Joe Paradiso:是的,不过这种转变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。
那时候,我就在思考传感器网络的未来。我们当时正在研发很多可穿戴传感器,这些传感器会与某个地方的无线电接收器进行通信。那时的传感器都是较大的物体,并未嵌入任何材料中,彼此相隔也较远。
我预见到有一天这些技术会变得足够“小”,我们就可以开始将传感网络嵌入材料中。所以,你可以想象传感器融入建筑材料、衣物等各种物品中。我们有很多项目都在朝着类似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的尺度发展,而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则将这种尺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,我认为这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突破。
甲子光年:传统的感知网络依赖于外部传感器,而智能纤维将计算与感知内嵌于材料中。这是不是代表了“AI物质化”的趋势?它是否正在重塑我们理解人机交互的方式?
Joe Paradiso:这是真的。
我和Cedric经常为此争论:纤维是一个理想的AI应用平台吗?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理想的大规模扩展AI的平台,因为它是一维的。AI需要多维的连接,更适合采用三维集成的方式来实现AI功能。不过,你也可以考虑将纤维排列成网格状,并让它们相互连接,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方向。所以,这并非完全不可能。
但作为传感平台,我认为这种纤维是非常棒的。在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之前,我们还做过几个版本的“传感胶带”。其中一种可以铺设在地板上,用于监测人们的行走情况,以及人们在建筑内移动的动态。还有一种的“传感胶带”就像一卷美纹纸,很薄的一层,我们可以把它贴在衣服上以及各种物品上,将它们变成交互界面。
下一步就是把它做成纤维的形态。我们当然可以在传感器中嵌入计算功能,而为了实现网络连接和低功耗,你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带宽占用,所以需要让处理器智能地管理数据传输。目前,这种纤维可能已经能够实现一些识别功能。
我认为它更多地用于数据精简、简单的模式识别,或者筛选出有价值、值得传输的信息,然后将这些信息传输到网络中。因此,目前纤维中的处理功能可能更多是处理基础数据、调节数据传输速率和降低功耗。
甲子光年:你的研究中常提到“the nervous system of the environment(环境的神经系统)”,我理解,这其实是把传感器、计算、AI和反馈机制嵌入环境,使其像“神经系统”一样持续地感知、理解和回应人类活动。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本身似乎成为了一个神经元网络?
Joe Paradiso:我会这样看待它,你可以看看大脑里发生了什么——这其实启发了我们称之为感知媒介(sense media)的许多研究,而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正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。
以人类皮肤为例,它有感受器,并带有向下延伸的神经纤维。但这些信号会在很多地方发生突触并进行局部计算,甚至在到达大脑之前,单个神经元内部就已经在处理信息。这样的机制会过滤掉无意义的刺激,对那些持续、重复、无关的信号逐渐忽略和适应。
类似地,我们的许多动作,比如走路,虽然由运动皮层控制,但大量信号处理其实发生在脊髓中。在信号双向传递的过程中,会不断发生突触并完成部分处理。
我认为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的工作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类似的。我们会有很多传感器,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,收集信息,信号会被组合、处理并不断调整。
甲子光年:未来是否会在纤维上实现完整的AI功能?
Joe Paradiso:我不知道,我对此持保留态度,不过Cedric想尝试这样做。
我的想法是:先把传感平台搭建好,看看它的性能表现如何,然后随着技术的扩展与成熟,再逐步把更先进的处理能力嵌进去。
我想再次强调,我不认为纤维是发展大规模AI的路径,但它确实为传感技术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。
甲子光年:你认为智能会向边缘侧迁移吗?
Joe Paradiso:智能最终都会往边缘侧迁移,这肯定会发生。
有一部分智能会出现在纤维里。但至少现阶段,我不认为我们会在纤维上跑那种非常先进的AI模型,只会跑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型。所以,纤维里会实现一些AI功能,但不会是那种特别复杂的。
当然,这些信号最终还是会被传到下一层的计算系统,比如云端,在那里做更深入的处理,并和其他数据融合。
甲子光年:听起来有些抽象。
Joe Paradiso:我觉得未来的趋势可以用一个生物学类比来解释。
我们可以在纤维里嵌入类似“蚂蚁大脑”那样的简单智能。你知道,蚂蚁本身就能做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事情,那如果我们能在纤维里实现类似的功能呢?
然后这些信号会被传到更高一级的系统,就像是“老鼠大脑”级别的东西,可能存在于连接这些纤维的衣物里。再往上,可能会有类似“猫的大脑”,甚至再更高层次的“超级智能”。
我当然不知道它最终会有多少层级,但大致的结构是这样:到了物理边缘(edge)这里,主要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压缩和预处理。它会做一些计算,目的就是节省带宽、筛选出真正需要的参数。毕竟如果有大量传感器,你不可能把所有数据一直传出去,否则系统会被压垮。
如果你用这种结构,你就可以智能地减少数据量,把真正有意义的部分留下来。
4.AI终有一天会“消失”
甲子光年:当AI可以实时感知我们的呼吸、体温与微动作时,我们是不是正在进入一个“被环境理解”的时代?
Joe Paradiso: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当然,我们至少正在进入一个周围的计算环境能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时代。
我们已经开发出了自适应房间(adaptive rooms) ,它能根据你对房间的反应,通过投影、音频等方式进行调整。所以,是的,我们的环境会开始更多地了解我们。
甲子光年:在睡眠场景里呢?
Joe Paradiso:在睡眠场景里,这其实是一件好事。因为它可以在合适的时间给你适当的干预,帮你获得更好的睡眠,甚至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。
我自己就是这样。我工作很努力,我想大家都一样吧。我经常是工作到眼睛都睁不开了才去睡一会儿,然后醒过来昏昏沉沉,再喝杯茶,继续工作。但这肯定不是最健康的方式。那么,如果有一个助手能提醒我“现在必须停止工作,去睡一会儿”会怎么样?
这种系统能通过量化自我的数据收集各种信号,建立上下文,甚至了解我的生活模式,知道我的身体是怎么运作的。这样的系统是可以帮到我的。
甲子光年:除了睡眠场景呢?我们现在就在MIT校园里,我能感受到,其实环境对学生学习也会产生影响。你感受到了AI对学习的影响吗?
Joe Paradiso:我觉得在学习领域,这一点尤其有吸引力。因为AI会成为非常棒的导师。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例子,比如学生用ChatGPT来完成作业甚至作弊,当然那不是好事,但同样的系统也可以成为真正的导师,而且是高度个性化的导师。它了解你,知道你掌握了什么、没掌握什么,而且它有无限的耐心。
现实中,导师时间都很紧张,总会有耐心耗尽的时候,而AI理论上不存在这个问题。AI会理解你的反应,知道你现在的精神状态是不是适合学习,知道该给你多少信息,以及应该用什么方式呈现这些信息。
所以这些系统,它们会无处不在地陪着我们,特别是在学习的时候。这种事情已经可以开始发生了。
当然,我也担心另一面:如果系统开始“灌输”什么,那就不好了。
但至少就“学习”这件事来说,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:信息会在最合适的时间、以最合适的方式送达给你。那些非常了解我们的系统,会做到这一点。
这会在健康、学习,甚至“我们对自己的理解”这些领域带来巨大的好处。
甲子光年:今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“碳硅一体”“人机共生”的新形态,“FiberCircuits”智能纤维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。你是否认为未来的AI系统会不再是“我们使用的工具”,而是“与我们共感的生命体”?
Joe Paradiso:我认为是的,AI终有一天会“消失”,不再那么“明显”,我们也不会再把AI当成一个单独的技术来看待。
我在之前的一些演讲里说过:智能环境会变成一种义肢(prosthetic),是一种“自我的延伸”。
比如,一个房子会努力让我生活得更舒服,为你节省能源、节省开支,让灯光帮我看得更清楚。系统会根据我的状态去调整,让我能更好地完成我在做的事情。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说,你会把智能系统看成一种“义肢”。
有了AI,我们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。我们始终保持连接,我们正进入一个“群体心智(group mind)”的时代。
未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可穿戴设备,于是就出现两个层面的问题。
第一,“我与他”的界限。“我”在哪里结束,“他”从哪里开始?因为我们的连接太紧密了。现在人们有时会作为一个社交连接群体来形成观点,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,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失去的东西。这种情况本可以变得更好,但目前来看并不理想。
第二,“我与云”的界限。不过那是下一阶段的事了,云端的智能不一定是人,可以是AI。
现在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:一个AI Agent会和我一起成长、一起进化,它知道我的偏好,知道我想干什么,知道在不同场景下应该怎么根据对我的理解来回应。
它最好是替我办事,而不是替某个机构办事——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另一个方面。
甲子光年:你认为,AI将会成为什么?
Joe Paradiso:AI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,而且是非常私密的一部分。到某个时间点,它会变成我们的一种延伸,就像我们在社交层面已经和云、和他人融合在一起一样,AI也会变成这一混合体的一部分。
所以问题又回来了:“我在哪里结束?云从哪里开始?”这是一幅动态变化的图景。它既令人兴奋,也令人害怕,但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(封面图及文中未标注来源配图由慕思集团提供)
 51692
51692 1416
1416 346
346 0
0